藝評
談何倩彤的抗爭情緒排泄,與馬琼珠的死亡陰影
梁寶山
at 12:42pm on 25th April 2020

圖片說明:
何倩彤於漢雅軒的個展「沼澤地」展覽現場。(攝影/何兆南,漢雅軒提供)
(This article,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, is a review of two exhibitions - ‘Ho Sin Tung: Swampland’ and ‘Ivy Ma: Poems, days, death’.)
藝博會取消,有人覺得天塌下來。我倒覺得是難得清靜,終於不談八卦,只談藝術。肺炎肆虐,香港大型藝文場館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博物館、西九文化區和大館的展演場地均閉戶關門。我卻更有閒心細看了幾個中生代藝術家的個展。沒有策展人議定功課,個展的出發點或許雖然個人,卻都切中當下香港的時代面貌。

何倩彤於漢雅軒的個展「沼澤地」展覽現場。(攝影/何兆南,漢雅軒提供)
何倩彤在漢雅軒的個展「沼澤地」,以黑暗迎接新春。是的,經歷了超過半年的抗爭,根本無慶可賀。幽暗的展場,除了繼承了何倩彤一向對「觀影」經驗的著迷之外,也令觀眾有如置身不可預期的危險之中。可是,「不可預期」指向的並不是還未發生的將來,而是仍然令人深陷泥淖的過去。這幾組各自表述,卻又互相關連的裝置和繪畫,均是關於一些徒勞的歷史,當中既有個人的、也有世界的。作品《死皮》是一組九件的裝置,「造型」來自恐怖電影中的「床單鬼」,何倩彤以國旗取代這件貼身之物,它們是已然「死亡」的滿州國、蘇聯、夏威夷王國、港英(英治香港)、東德、羅馬帝國、比亞法拉共和國、奧圖曼帝國和琉球王國。這些大部份只曾在歷史書中見過的旗幟,真的是已成過去?還是依舊陰魂不散,甚至歷歷在目,左右著我們將來的命運?自抗爭運動開始之後,香港發生多宗離奇而不作追查的死亡個案。[1]「不可知」的恐懼與手足之情所帶來的,是身體性的切膚之痛。

何倩彤《死皮》(Dead Skin),混合媒介,尺寸可變(每件約:90x60x60cm),2019。(藝術家及漢雅軒提供)
另一組混合媒體作品《舊史》,何倩彤反其道而行,把自己與前度「共同體」的遺物公諸於世。這些可能還曾伴隨著花言巧語的糖果、藥物和巧克力,不單滿足觀眾對「女」藝術家八卦的欲望,何更落落大方地把它們放在精美的透明玻璃器皿裡。糖果與藥物,其實都是刺激身體情緒的化學品,與黏土混合造型,產生出來的顏色與形狀卻更像排泄出來的大便。把已經腐朽的東西排出體外,自是正常的身體反應。但這些有著巧克力成份的大便,不正是香港「一國兩制」的縮影嗎?種種以糖衣包裹的選舉方案,倒頭來都是對具正常腦袋的市民的侮辱。無論是「勇武」抑或「和理非」,這九個月之後,均已深明中共給我們的選項,不過是巧克力包裹的大便,與以大便包裹的巧克力之間的分別。

何倩彤《舊史》(Same Old Sweet),混合媒介,尺寸可變(一組五件),2019。(藝術家及漢雅軒提供)
何倩彤選擇以黑暗讓幽魂乍現,馬琼珠則用光明來呈現死亡。二人的出發點也許個人,觀察的結果卻是社會性的。中生代的馬琼珠,是已故前輩畫家關晃的學生。關晃近乎單色的油畫擅於以微妙的調子捉捕光影變化,馬琼珠早期創作亦以繪畫為主,後來才轉向物件和裝置,表現怪異的身體和空間感知。近年她又回到表像和媒介,例如重繪電影定格、收集現成影像。繼2018年在富德樓小型個展「時間曾經打一個摺」後,她似乎終於成功摸索出一條畫家式(painterly)空間裝置的方法,讓光影溢出邊框,對裝置空間作更為整體的調配。這次在光影作坊新址舉行的個展,以光影來詰問時間與生死,對生命作出的哲學反思,讓牆壁變成光影變化的載體。《缺席父親的喪禮》,父親的肖像變成了過千個像零錢般大小的貼圖,用釘子懸空吊起後逐一釘在一整面白牆之上。生命的唯一以陪數放大,同時卻又何其渺茫。相反,對於陌生人之死,馬琼珠卻沒有冷眼旁觀。無家可歸的「麥難民」,在快餐店的角落失救猝死。[2] 這些無家可歸的邊緣人,被社會視而不見,最後更被「無形之手」(invisible hand,亞當.史密斯 [Adam Smith] 對資本主義的比喻)謀殺。作為描繪影像的人,馬琼珠以三個小幅反覆重現這位名無家者的葬身之所。三幅黑白畫面,取材自模糊的新聞影像,馬琼珠透過重覆繪畫來重訪這位被不聞不問的無家者,更用幾何形狀來給畫面貼金,對這宗無聲無息的死亡個案作最後致敬。

馬琼珠的作品《缺席父親的喪禮》(局部)。(光影作坊提供)

馬琼珠的作品《缺席父親的喪禮》。(光影作坊提供)

馬琼珠的作品指出無家可歸的「麥難民」,被社會視而不見的情況。(光影作坊提供)
「詩,每天,死亡」只有五組黑白作品,卻完全充填了整個空間。原來平面的攝影作品,給堆疊在地上,因而獲得了體積,並且在空間中造成光影。而與「麥難民」相對的,則是一幅巨型安德烈.塔可夫斯基(Andrei Tarkovsky)的《潛行者》(Stalker)電影定格。這個在影片最末的鏡頭,片中的殘障女孩竟然發揮出超能力,爬在桌上用念力移動了杯子。巨型定格,與「麥難民」的最後影像,一大一小地佔據了整個牆壁,大量留白卻合成意味深長的雙連畫。

馬琼珠於光影作坊的個展「詩,每天,死亡」展覽現場。(光影作坊提供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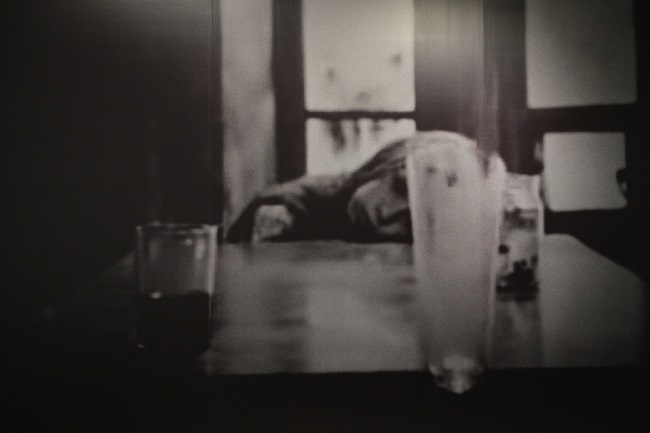
馬琼珠的作品中與「麥難民」相對的,則是一幅巨型安德烈.塔可夫斯基(Andrei Tarkovsky)的《潛行者》(Stalker)電影定格。(光影作坊提供)
何倩彤與馬琼珠兩位藝術家同樣把非常個人的經歷加以放大,卻成功表達出整個城市正在面對的不可抵抗力量。
註解:
[1] 除了像去年8月31日發生的警方在地鐵擊示威者事件外,自去年6月「返送中」浪潮以來,香港還發生多宗「沒有可疑」的死亡事件,而「自殺」數字達256宗,較前年同期增加34宗。雖然死狀令人懷疑是由他殺所致,但警方一律不立案調查。令人懷疑死者或為嚴刑及謀殺致死。
[2]「麥難民」是指一些無法負擔昂貴租金而被迫於例如麥當奴等24小時營業快餐店內的無家者。2015年10月,一名經常棲身於九龍某公共屋邨麥當勞的中年女性,看病之後一直在快餐店角落的位置坐著不動,直至七個小時候才被食客發見已經死亡。該事件引起社會嘩然,但高企樓價仍然持續高企,社會保障亦無改善。2018年9月,另一名46歲無家者再次在另一所位於油麻地的麥當勞廁所內猝死。
原文刊於《典藏》,2020年3月20日。
